曾雇 35 万员工的汽车帝国, 如今市值竟不如一杯咖啡!
- 2025-07-05 13:16:48
- 116
美国汽车工业的兴衰故事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从曾经的辉煌跌落到濒临破产,再到试图通过策略调整重振旗鼓,却又在新的市场竞争中面临挑战。这一切的转折,要从 2008 年那场震惊全球的金融危机说起。
2008 年之前,通用汽车的股价曾高达每股 103 美元,市值接近 600 亿美元。但到了 2008 年 6 月 2 日,通用的股价暴跌到令人震惊的 1 美元。
这意味着什么?这家曾雇佣 35 万员工、年收入超 1800 亿美元的巨头,市场价值竟然还不如一杯咖啡。
福特和克莱斯勒的命运同样惨淡,三家公司的合计市值从鼎盛时期的数千亿美元跌至不足 100 亿。
股价暴跌的背后,是美国汽车工业早已失控的成本结构。当时,一家公司的劳动力成本能占到产品价格的 8%,养老金负债超过现金流,研发投入也无法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这些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几十年积累的结果。比如 20 世纪中期,美国汽车工业享受着低监管成本的红利,在利润丰厚的市场里运营。
但到了 60 年代初,环境和安全立法改变了一切,新法规要求制造商在 1975 年前将排放量减少 50% 以上,这意味着巨额的研发和生产成本投入。
与此同时,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进入美国市场。1958 年丰田皇冠进入美国时,带来了不同的成本结构和生产哲学。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更暴露了美国车企的成本效率问题 —— 能源价格波动让消费者转向小型省油车,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五年内增长超过两倍,1980 年达到 65 万辆。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制造商做了一个关键选择:在政府政策激励下,将资源投入到卡车和 SUV 领域,因为这些车型的利润率更高,但这也暴露了他们对长期市场趋势的误判。
而日本制造商专注于乘用车市场,到 2006 年,《消费者报告》评出的十款最佳汽车全部为日本车。
美国车企的高成本结构还体现在劳动力上。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虽然保护了工人权益,却也让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养老金、医疗福利等让劳动力成本占汽车价格的 8%,而日本车企因非工会化降低了这一比例。
此外,美国车企对本土生产的依赖,限制了他们利用全球低成本资源的能力,这与日本车企的全球化生产策略形成鲜明对比。
2000 年代能源价格再次上涨时,历史重演,消费者又转向经济车型,主要选择日本车。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生产数据持续下滑,比十年前下降近 50%,这不仅是市场份额的流失,更是整体成本竞争力的缺失。
2008 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放大了危机,当时约 24% 的汽车销售通过房屋净值信贷融资,房地产市场崩溃后,汽车消费的信贷基础也随之坍塌。
面对绝境,三巨头的高管们放弃私人飞机,开车前往华盛顿,试图证明他们的困境。他们声称,汽车工业崩溃不仅是底特律的灾难,更会危及整个美国经济,因为这会波及供应链和经销商网络。
当时他们已经耗尽了 180 亿美元的信贷额度,账户里没钱维持运营。尽管最初救助方案在国会投票中失败,但随着破产威胁加剧,最终还是批准了 170 亿美元紧急资金,奥巴马任内又提供了更多资金。
救助带来的是彻底重组。通用汽车宣布破产,旧公司变成汽车清算公司,将有价值的资产和品牌出售给新的政府支持的通用。
通用大规模裁员,关闭了悍马、庞地亚克等品牌,一年内出售萨博,工厂数量减少,美国员工裁员三分之一,高管职位削减 35%,并承诺制造更省油的汽车。
克莱斯勒也采取类似策略,专注于道奇、吉普等有效品牌,并与菲亚特合作。福特虽然没要联邦资金,但也出售了阿斯顿・马丁等豪华品牌,专注于福克斯等车型开发。
当时人们以为这是一个新开始,但没想到十年后剧情反转。2018 年,福特宣布除了野马,退出在美国市场制造或销售任何乘用车,蒙迪欧、嘉年华、福克斯等都不再生产。
而克莱斯勒早在 2016 年就结束了道奇飞镖等经济型轿车生产,只保留肌肉车和豪华车。通用汽车到 2020 年代也宣布停止生产多款轿车。
三巨头几乎完全停止为美国市场制造轿车,这背后是一个被称为 “SUV 漏洞” 的法律技巧。
这个漏洞源于 1970 年代的立法,当时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对乘用车设定了较高要求,但对 “轻型卡车” 的定义模糊,只要符合运输财产或人员、设计用于越野等模糊特征,且重量在 6000 磅或以下,就能被归类为轻型卡车,享受更低的燃油经济性要求。
加上 1964 年对外国卡车征收 25% 关税的 “肌肉税”,SUV 和卡车成了国内车企的安全港。更重要的是,SUV 的利润率高,虽然体积大,但额外材料成本微不足道,车企便将高利润的 SUV 和卡车营销为更安全可靠的必需车辆,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策略和营销创造了消费者对 SUV 的需求。
但这种策略的代价是全球竞争力的丧失。如今三巨头只占美国汽车工业的 40%,与辉煌时期相距甚远。
消费者也不再信任他们,2024 年的召回数据显示,克莱斯勒、福特、通用分别发起了美国汽车品牌中最多、第二多和第四多的召回。
2025 年,没有底特律品牌进入《消费者报告》汽车可靠性排名前十,过去三年只有一次三巨头品牌进入前十一。
质量问题还不止于此。克莱斯勒在 2010 年代卷入排放测试丑闻,2014 年至 2016 年的某些吉普和 Ram 卡车被发现违反排放标准,最终导致超过 10 亿美元的和解和罚款,甚至对欺骗排放测试的阴谋认罪。
通用汽车的 L87 发动机丑闻也很严重,2025 年召回约 60 万辆搭载该发动机的车辆,而消费者早在六年前就开始投诉发动机在 10 万英里内出现灾难性故障,通用内部调查了三年却无结果,直到监管机构介入才发现问题,甚至有 12 起撞车和 42 起火灾可能与此有关。
三巨头的短视策略在合并后依然存在。比如克莱斯勒与 PSA 合并成 Stellantis 后,2023 年创造了 200 亿美元利润,向股东支付 75 亿美元,CEO 年薪 4000 万美元,但这是通过大幅涨价、裁员和关闭工厂实现的。
短期利润最大化的代价很快显现:工厂工人罢工,品牌因偷工减料声誉受损,新车滞销,但策略仍未改变,2025 年又进行了一轮裁员。
当底特律三巨头依赖政策漏洞和短期策略时,新兴企业正在开创新时代。特斯拉在 2010 年代和 2020 年代初主导美国电动汽车市场,作为一家从头围绕电动车建立的公司,它比传统车企更有优势。
外国电动车品牌也在推进美国市场,现代、起亚用便宜的电动车蚕食份额,日本车企也准备推出美国电动车。
2024 年美国销量第一的车辆数据更具象征意义:几十年来第一次不是福特 F-150,而是丰田 RAV4。
这意味着在美国专门设计让本土公司受益的轻型卡车类别中,美国人却更信任日本车。当特斯拉的市值超过三巨头总和时,资本市场也给出了判断:投资者选择了创新而非保护,选择了未来而非过去。
如今,电动车转型的成本、中国制造商的崛起、自动驾驶技术的突破,每个变量都可能重新洗牌汽车行业。
底特律三巨头能否在新竞赛中找到位置,还是会再次寻求政府庇护?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几家公司的命运,更关系到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当我们看到街头驶过的巨大 SUV 时,或许该想想这背后隐藏的经济密码 —— 依赖政策漏洞的短期盈利,终究难以在基于质量和效率的市场竞争中长久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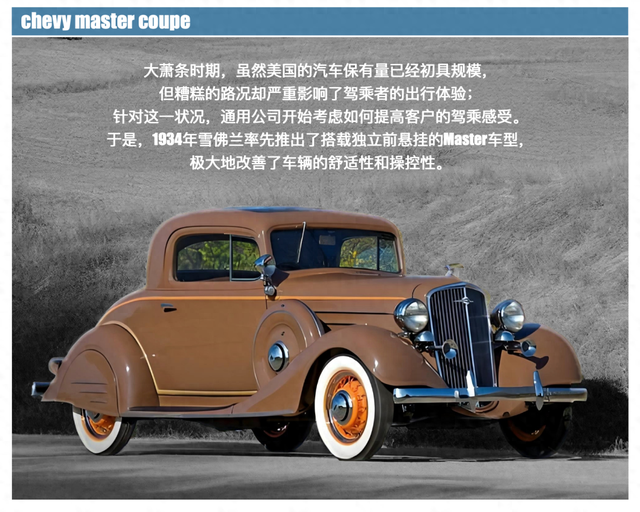
- 上一篇:张晋李承铉胡夏早安你们是来搞抽象的吧
- 下一篇:樊振东比林诗栋
